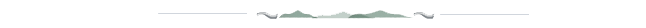我陷入一场虚构
平湖并没有秋月
只有一场空洞而苍白的叙述
只有这冰冷的风塌陷在无垠的水面
我看见湖面上升腾的乌鸫
消失在这苍凉的草丛
秋虫的嘶鸣像一个被扼住咽喉的人
想要发声
却被这突来的夜景
惊愕
湖水的声音如此悲切
从空洞的修辞中不断地叙述着
一场雪从虚无到厚重
直到轻盈的翅膀被冰雪覆盖
克丽克的文字显得过于冗长
晶莹的冰雕透过密集的雨声
在通透的土地上横行
粉色蝴蝶在细嫩的繁枝上低吟
我忘了该怎样地驱逐这浓烈的火焰
佛光 青灯 莲花
巍峨的大殿 雄伟的佛像
身体里亮彩的经文早已剥离鲜妍的花簇
九问 九天
在风雅颂中失去家园 失去阳光
失去烽烟下烈马的角逐
戛然而止的唢呐
在西风里不再为相思折眉 负气
苦难 离索 流浪
像是这个世上所有的种族歧视
被一消除
此时我打开一个空洞的躯壳
从躯壳中取出绚烂的花盏
或许我能做的仅仅如此
又是秋夜
当所有的意念凭空消失
我从冰冷的月色中走向深渊
走向令人痛彻心扉的北极亦或是南极
是这些无辜的星儿牵扯着我的臆断
还是我的判断过于武断
在这个薄凉的悲秋
让我过早地对一些昙花产生厌倦与不安
从今天起
是的就是现在我必须学会从容学会淡定学会忘却
我需要学的还有太多
比如忘却玫瑰的光鲜
沙漠的荒凉 戈壁滩的沉寂
比如如何应对一只蝴蝶的死亡
一只蚍蜉的衍生会给生活带来的欢愉
在生活的阴暗面跳舞
在馥郁的花丛中为一只野蜂唱歌
在静默的灌木丛学会抽烟
所有的联想比一朵花盛开更为迷人
在洁白的米缸里我看见可爱的米老鼠穿过我发出暗香的九月菊
放下太多的心事
从容去面对峭岩上冲下的瀑布
哪怕是小小的响动
带来的忧伤
不必过问 不必挂怀
夕阳里的倩影
像宇宙里无穷的生灵
充斥着对黑暗的恐惧
对人世的敬畏
甚至我用一整个冬天期盼一场皑皑白雪
将我裸露的躯体掩埋
我不敢面对一颗恒星的陨落 消失 沉没
大地上一些繁盛的事物
让我感到我做的事物
如此危险
比如在深夜倾听远方的丛林传来兽类的呼号 呐喊
我的危险远不止这些
我想用这些寂寞的雪为你打造一座辉煌的城池
还想驱走那些留在苍穹里泛着黑缎般厚重的云彩
不必点燃黑夜中的喧嚣与繁华
星星是落进内心的填充物
像黎明前那些潜伏在河床底部的秋虫
风只是轻轻的晃动
那些寂寞的秋虫
便在我迟疑片刻
从菖蒲里消失直到梦被风
吹醒
镜中
我不知道我对昨天
说了些什么
那些风便不再张扬
我开始用一整个夜晚去沉思
或许我只是秋夜的莽原一只空荡荡的躯壳
在我腐朽的躯壳上安放着枪支弹药
也放着一些厚重的经卷
在苏北洋河这个不起眼的小镇
我看见一群蚂蚁在陈旧的秋风中经过
我无法喂养它
就像我无法面对我死去的父亲
如果一杯酒能够叙述黑暗
那些轻轻掠过的花盏总是在我的诗行中拒绝开放
拒绝以一种另类的美感
投入一场冰雪的覆盖
像是父亲病入膏肓时
我买回的车厘子
在这个盛产美酒的小镇
我却想起一只灰色的斑鸠或许是别的鸟类
每一次阴风袭来
我必须学会在父亲的药方里加入黄莲银翘 白芷 熟地
我听见这个整夜微微的雨逼近父亲虚弱的体内
而我仿佛看见我的药方
洒落一地
像美丽的格桑花铺陈着梦里每一个黑暗的角落
我开始在黑色的夜
掏出手枪 也 掏出一些祭祀用的白烛
花朵
和一些光滑的鱼
我知道那条黑鱼不适合祭奠我朴实的父亲
微弱的星光轻轻地落进这场悄无声息的葬礼
我虔诚地跪拜 叩首
企图用雪表达父亲不屈的一生
冰冷的雪花 微黄的菊盏 洁白的纸鹤
还有那黑色的棺椁
流淌着父亲腐败的尸体
那些坚硬的残骸
像是整个夜晚飞翔在院子里的
乌鸦
像是黑暗诅咒着深夜
我泛动的酒杯在月光里迸裂
而我却听不到人间有任何悲伤
这或许是我虚构了一个夜晚
今夜:无法入眠
我以任何一种方式拒绝这个深夜饱含
合金的月光
就像拒绝去读一首爱易丝关于月光的描述
死亡 罹难 流亡
与战争
这些使我不安的词汇
总是在我身体里成长
我听到烈火焚烧的声音
听到一朵花在深秋发出无助呐喊 嘶鸣 彷徨 恐惧
而我的手中却铺阵着玫瑰 巧克力和驿动的词汇
我飞奔的黑马
温柔的姑娘正高举着那簇像征爱情的茉莉
洁白的超乎了我的想象
如果我的土地开满了鲜花
请翻开我
悲郁的诗卷
那里依然有牧羊鞭儿掠过青草的声音
我听见有什么东西止步于我的车马
我从容地从行囊中取出一卷卷泛黄的心经或者别的经书
如果此时你恰好经过
请絻起你美丽的长发
将滴落在白纸上的蝴蝶残骸收进那片
燃烧的阳光
不要谈及死亡
我永生的魂魄就驻在月光的胸膛
(作者:耿兵2020-10-21发于现代诗歌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