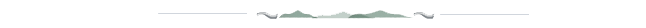有只鸟儿叫“神奇”
在火车站飞,一只鸟儿,翘着尾巴,
它不作声,却知道何时张开了羽翼
它四下瞧,清楚要在山林里鸣唱
清楚夏日里筑巢,冬日风雪中猫冬
这只鸟儿,有夜蛾扑火的品质
暗夜会扑向灯光,天明枝上亮尾
我不知它叫什么鸟,它活得透明
鸣声极其地神秘,我就叫它神奇
它像只山雀,飞翔在阿尔山的上空
它落在笔尖上,向枝头叽叽鸣叫
它翱翔在语言中,在诗句中跳舞
他不是鸟儿。却比鸟儿的视野宽广
啊,神奇落地,啄阶下的小石头
它与雪中的麻雀一起啄一棒小米
别的鸟飞走了,神奇没有飞
依旧在啄,用了写一首诗的时间
夜半,站在阿尔山火车站
夜色中,大熊星座暗蓝的光茫下
阿尔山火车站,站立着像个雕塑
这幢东洋低檐尖顶的小楼
用阴影笼罩着我,我就像块山石
作为楼基拼砌在花岗岩的石墙下
呵,黑暗与星光的世界早刻在我的
灵魂深处,许多往事如磷光在闪烁
像梦萦绕在云际。常记得父亲谈起
那些火山湖丶堰塞湖,还有这温泉
以及温泉传说中闪动银光的小白蛇
这个小站,六十年来让我活在父亲
的童话里,在日本殖民的时代
他在此渡过十四春秋,今天我来了
火车站还是旧日的容颜,哈拉哈河
流着,它没有吞噬身边的那尊雕像
站在这星月下,望着正安睡山中的
小车站,看着那黄墙红瓦的屋顶
仿佛百年的山火正点燃,让我重温
父亲沙砾般一生,头顶是大熊星座
身边是压弯脊背的母亲与三个儿子
岁月面前一切都会改变,可这车站
却未变,哈拉哈河冲走了山中无数
落叶丶枯枝,也冲走了小站前站立
的父亲丶母亲的一生,当然它一直
在奔流,势必有一天也会带上我……
黑暗中,没什么不会被带走,除了
阿尔山,也许有一天火山湖、温泉
也会被带走,等到作为历史遗址的
阿尔山火车站也不见了,惟头上月
天宇上的大熊星座还会凌空地辉耀
梦中的雪
梦中的雪,是从你灵魂中飘过来的
像父亲一样从极北的山峦间走过来
咳嗽一声,就落下了雪团,一团团
母亲用木柈生火,雪在炉膛不融化
鸟没地觅食,丢一把米,它们飞来
落在雪上,有冻僵了,有的已死去
梦中的雪,父亲伐木的锯声从南向北
额上摔成八瓣的汗珠留在松林枝叶间
其中一部分和扬起的雪尘进入棉袄内
虱子会在发梢钻进钻出,不怕人的
气得哥哥醒来后在袄的缝隙进行围剿
嘎吧,不是雪花,大拇指上的是血滴
梦中的雪,是父亲大头鞋追逐的嚎叫
狼在北方山林没有食物会到村落觅食
狗听到动静,就会狂吠,父亲不怕狼
他有打狼的本领,狼有脚印,尿味
雪中木门推开了,一线光,父亲出门
梦中的雪,那只狍子,就立在风雪中
见人,害怕会跑,跑了再回来,等你
等到雪满山沟,盖满林子,铺平脚印
铺满河床,盖住村落,堵塞了道路
等你找不到喘气的太阳,除了那狍子
你永远不要想在林中见到熊、蛇……
梦中的雪,并未融化,父亲不在北方
母亲也不在北方了,哥哥也不在北方
每当漫天大雪,你就会到南方大海边
那里是不下雪的,梨花开了也会像雪
只有梦中,你才会走进极北的山峦中
现在我在铁锅里,翻炒着梆硬的雪花
那是来至极北的山林,那里酷寒
不管你怎样加火,铁锅烧红
也难捂热,因为它来自极北的山林
它曾与父辈们住在山里,八月开花
雪,虱子般落在纸上,掐不完,没血
一株颤抖在山下的树
我家窗外有一棵树,它足够的敏感
虽没消息树知名,却常簌簌地颤抖
像我不安的灵魂,容易受到了刺激
夜半为安慰它,我将头伸向夜色里
害怕地祈祷,让树免受刀锯的威胁
又担忧痛楚,怕白蚊蚕食树的根系
黑暗中,我在历史深处中沉思冥想
并为历史人物的遭遇而呐喊,发声
并没有西北风,树冠就急剧地抖动
啊,抖动的树呵,也许我错怪了你
心头的飓风刮过狼群嚎叫的阿尔山
磅礴的正气也无法保证你不会颤栗
(作者:肖振勇2021-11-30发于现代诗歌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