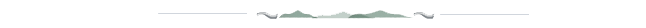我在朝北方张望
在白昼、在黑夜,很长的岁月里
我在心里提醒自己朝北方张望
不只是用眼睛、大脑
还要用思想、灵魂的力量
我知道,那向往的北方实在遥远
不可能有全部抵达的希望
我知道,艮古的荒芜还没有聚落
残破的断碑倾泻着银丝样的月光
在双眼不能触及只接受灵魂的考量
一棵老榆树晃动一截摇曳的丝缰
淤泥的河畔,睡着空荡的毡房
裸露的沙丘,半露出锈蚀了的铁枪
啊,北方,我目光投向之地
我看见晨曦中显现的山峦突起
一个女人驾着勒勒车
长调在云空中回荡
拉车的骆驼跑着扬起漫天的昏黄
呱呱,一只乌鸦从桦树林扑翅而飞
绕着一个仙人柱尖利的歌唱
吁天人敲着神鼓模拟狼的舞蹈
无数灵魂驾着神鹰在夜的帷幕翱翔
啊,北方,目光所及之地
从沙海跃起穿着13世纪皮甲的勇士
紧策着骏马,朝着黑林子奔去
瓦砾上,篝火的痕迹飘着烤肉热浪
呵北方,北方,我的灵魂所系岁月
我思想的旌旗,飘在干裂的兽皮上
那浸着熊、虎、鹿的血迹的大纛
有千万匹骏马,千万柄铁矛在闪光
向北张望,在不是梦境中搜寻梦境
向北张望,在日落沙丘瞭望瑰丽的霞光
我的心于北方有某种宿命联系
为一次漫长的旅行,执着地跋涉在路上
和林:神龟流落的城垣
呵,哈剌和林[1],无法再见到你的城垣
像古埃及、巴比伦、古罗马被人忘记
我今天寻找你,只面对冷冰冰的神龟
让我翻开一卷古书,像午夜的星照耀
着荒凉的大漠,照着一只驮碑的石龟
那龟爬着,那深邃的眼窝藏着滴泪水
龟在哭呀,安放的背上的圣旨碑哪去
谁能证明和林城的存在,写着大海汗
窝阔台名字的碑不在,城也失去归宿
爬的神兽,无法释怀脊椎上驮着御碑
的失去,它爬着呀,从砂烁中巴望着
寒月冻结的银辉嵌入它闪着泪的眸子
它爬想证实黄金家族的主人曾在这儿
可脚下沙砾失去重量,连远处的庙宇
本地的牧民也不相信这流沙下的历史
承载过大汗都城的哈拉和林陷入流沙
苍鹰已逝刻着窝阔台名字的帝都失落
石龟不能开口,眼前帝都只剩下沙石
白玉为门,黄金为墙,大理石的殿宇
深深的内宫,亚欧大陆君主们膜拜的
汗座,那运宝石、黄金的船只哪去了
征服时占有过的,将在被征服后失去
明成祖怀着仇恨,北临大城,像项羽
对阿房宫一样,将这城燃成漫天火炬
哈剌和林,我梦中描绘过你,却无法
目睹你的城垣,只能对着冷冰的神龟
此刻谈起你,像谈论昨晚落山的夕阳
闪电河
在夏日来上都,古城内满目断瓦残垣
唯有闪电河,在草原画出婉转的弧线
让每个拜访上都的人沉醉于鸟语花香
沐浴得河风,倾听着鸟鸣喜上了眉尖
北岸,一串锈蚀翠绿的铜铃露出笑脸
俯仰间,地底数百辆帐车辚辚地出现
该把铜铃系在大汗辂车的哪匹服马上
六匹马,风吹马首都叮咚地叩响天边
闪电河,挎包内《藏春集》作者是谁
你会记得的高高的个子,聪慧的亮眼
当年刘秉忠奉旨寻找龙脉,那天累了
让人河上捕鱼、烹菜,自己高卧云间
闪电河呀,你北系着大漠,南衔居庸
像金莲川样闻名,并与九十九泉相连
满野的鸿雁,惹辽、金帝王纵马弓弯
也让元世祖对这孺子的折子连连赞叹
站在闪电河与上都之间,太阳亮闪闪
照耀着绿草之间五光十色的琉璃构件
照耀着两米长发黑的汉白玉的华表
照耀着华严寺彩色的庙宇仅存的屋檐
芦笔呀,我已无法描绘上都昔年盛况
千骑拥着象辇,宫妃伞下一张张笑脸
四月北狩,九月还驾,天子座下只剩
宴饮的记录还留在元人诗词歌赋之间
我知识浅薄不能一一叩问远处的青山
面对深埋的石础也绘不出连绵的宫殿
只觉得上都城没死,闪电河怀抱明珠
清澈河水奔腾向东,大都城还在东南
[1]哈剌和林是窝阔台建的都城,遗址在蒙古国乌兰巴托以西220公里处,遗址只有一只石龟。
(作者:肖振勇2021-12-01发于现代诗歌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