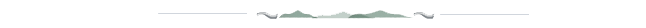◆高原宽容所有粗犷和率性的横行
整夜潜伏在山腰、成群结队的白云
如一根根横挑着大山的杠子
清晨,听见太阳从近在咫尺的天边
发出尖利的鹰啸
这群白云便在响彻牧场的响鞭中
开始一步步腾挪。它们很重
大山不停地把它们从左肩换到右肩
右肩换到左肩,直到它们登上山顶
在云团的掩护下,白色的羊群
黑色的牦牛群横着,一步步逼近雪线
高原的风打着横,吹过来吹过去
高原的太阳,红在卓玛们的脸庞
高原的白云,系在康巴汉子的腰间
他们在晚风中前俯后仰地跳舞
围着想象中熊熊燃烧的篝火
他们长长的手臂鹰翅般地横着伸展
藏袍带风,横扫草甸横扫坝子
高原辽阔得足以宽容一切横向的伸展
足以宽容所有粗犷和率性的横行
如果不能在天底下无边无际地横亘
所有的高耸入云,都不过是细足伶仃
◆只有在雪域高原,海拔才值得铭记
只有在高原,海拔才值得铭记
每一串深红的数字,刻在我能触摸的山石
召唤素无野心的我,去得寸进尺
而附近一定有一两座雪峰,傲视众生
制止所有攀登的底线,不在脚下
竟然划定在天穹之上
而雪线以上,森林已经浑身针叶
如刀、如剑、如戟
蜇痛因缺氧而扭曲的足迹
属于冰雪的,还是交给冰雪来铭记
而我们,只能留下一垛小小的玛尼堆
留下一顶锥形的风马旗
把我们渺小稀疏的足迹
在每一个值得纪念的地方,打一个结
即使不得不放弃前行
也要把失去车轮的骨架,留在路边的
石墩上,还保持着车的样子
凝视着别人的奔驰
◆要么崇拜,要么畏惧
蓝色的波涛,遮掩海床与深渊
高原,却毫不掩饰它
一个劲的高耸,一个劲的幽深
崇拜与畏惧,仅仅在电光石火之间
便能来几番剧烈的折腾
我的心终日在巨大的落差里
咆哮,跌宕着折断,高昂着匍匐
任何生灵,在高原上都十分渺小
即使雄鹰即使兀鹫即使雪豹
因为一直仰视雪峰,白云
成为一顶顶掉落在地的冠冕
因为一直俯瞰雪原,双目
最终对任何光线无感
如果生来就在雪山,就在荒原
只有崇拜,才经得起摩天的崇高
只有匍匐,才经得起雪原的辽阔
人们背上驮起一座座寺庙钻进云层
有路无路,脚下和膝下都是虔诚
有风无风,都是不能停止翱翔的鹰
遥望连绵高耸的雪峰,全部是我
向蓝天举起的一片白旗
臣服之心,不含一丝杂质
◆ 在雪山之巅
站在雪山之巅,狂风吹走云冠
高耸的巍峨无疑是一种压力
压实冰雪、压实我粗重的呼吸
踩扁那些石缝中幸存的枝叶
找不到支撑的身体慢性地恐高
凭空无依的俯瞰,有时是一种煎熬
不如站在海底的深渊里仰视
谁也看不见我站着还是匍匐在地
前头是无穷无尽的高耸与巍峨
即使站上万山之巅,即使触摸到云底
我们与浩瀚苍穹的距离
并没有因此拉近,与无垠的天空相比
海平面上一万米,与海平面下一万米
没有区别
◆钢铁的掌心,一朵格桑花
他一直钢铁着,钢铁到牙齿
总是让履带最狰狞的一面坎坷自己
即使这样,他还是不可避免地
压塌很多走过的路,压塌自己
在咆哮的江岸多余地轰隆
在满坡乱石的危崖上寻找坚定
独臂老兵
一只铁掌坦然朝天、俯仰天地
那只手掌,为什么一直久久地摊开
决非亘古冰雪,冻结了握拳之力
而是因为
掌心正中,有一朵鲜艳的格桑花
这朵小花娇艳欲滴、很重很重
重得要用全副钢铁之躯
才能托起
作者简介:本名龚炜,曾任教于黔渝两地高校,重庆市作协会员。在报刊和网络媒体发表诗歌、小说、报告文学、散文等约30万余字,有组诗曾被《新华文摘》转载,或收入《抒情短诗百首》《贵州诗人四十年》,曾获贵州省文联创作二等奖。
(作者:李之邨2024-07-20发于现代诗歌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