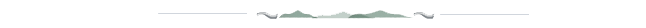马沙滩
壶源溪水快进入富春江时
在马沙滩歇下了脚
滩上有座龙潭庙矗立
护佑着延绵数里的两边商铺
江上商船如织,鱼贯而入
伙计把一把算盘打得啪啪作响
店老板笑脸相迎商来客往
时值1937年日寇炮火凌厉
逃亡的民国县政府
褪了一层又一层脚板
终在这江南一隅安了下来
一时人声鼎沸场口十里繁华
文昌阁被天南地北商贾吵醒
场口话从岸边钻入溪中,与溪中
商船上来自遥远的方言交换音节
货物在多事之秋卸装进出
外面浊世戡乱纷杂
场口成遮风避雨的小上海
大宗的票额汇入马沙滩
有税局设此而收得盆满钵满
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
场口的繁盛才渐渐消散
如今,我站在马沙滩广场
龙潭庙前的水还在缓缓流着
健身的居民跳起了《好日子》
一些鱼跳出水面又潜回水中
像一个个散开又合拢的历史涟漪

青江口
那些流回故地的祖辈童年
在时间斑痕里一次次深入年轮
这代表痴恋箴言的深度洗礼
春水潮动的巨响引发激素外溢
岁月的驿动在时代烤箱里烧涌
它擦落羞涩的黄昏锈斑
暴露出黑夜的波浪与粗鲁
等信人停在春江分割线暗影里
心中的墨汁泼洒无章法的写意
而青江口仍站在江水的身旁
因静默而变得更加纯粹与包容
像深埋泥中隐身修行的女儿红
在气味吹奏中运行着醇厚的弧线
整个村庄散出甜蜜的江南暗喻
抒情小楷枕着春水的清冽和素净
用温度去填满遗失的一阙冷词

六谷湾
被诵读声一遍遍扫荡,被早起的
晨曦一次次包围。这里
所有的事物都已习惯深埋头颅
只有鸟儿不太安份
它们筑巢、嬉戏、采食
俨然也成了静谧的一部分
只剩鸟鸣向树际漫延——
想攀到树梢,瞭望外面的世界
有些树老了
老到不忍心叫出它们的名字
可树下的草根还太稚嫩
需要陪伴与呵护
所以,六谷湾
生来就是一双伸展的臂膀
抱拥着欢笑、过错、青春与烦闷
如若不信,可问一下拂尘的清风
它一定知道湾里深藏的秘密
从少年到中年
将六谷湾杠出去又背回来
我绝不做匆匆的过客
因为,六谷湾
把它的辽阔与深邃都给了我

东梓关
远远望过去
这无非是一个普通的村落
走进去一转弯,你会看到一条江
一江春水,豁然让村落生动起来
走江边,会发现一座越女庙
江水在侧,香火敬水东流
沿江一瞥,就赶走了十万吨重水
只留下几缕波光、几朵白云
这时,埠口几只渔船也靠岸了
开始卸下劳累,还卸下了
半江烟雨、一船江鲜、二两薄霜
往村中心走,还会看到许家大院
民国的许家主人遍洒歧黄医道
在春和堂曾为郁达夫把脉开药
先生一篇《东梓关》
时而下笔很重,颓废家国的担扰
尽沉笔端。时而下笔很轻
怕只想留住这乱世中的一角恬静
而今,江鲜大会尽展农家鲜美
回迁房勾勒出吴冠中的江南水画
一幅现代富春山居图正徐徐展开
后来我查阅资料,得知东梓关
是由古代水上关隘发展而来
历史古迹、人文血脉,比比皆是
于是我写道:
一个村落,人水映衬,积淀古今
至今还泊在富春山水的悠然里
正如我身体里
一直驻着一份亘古宁静的心境

洋涨沙
在洋涨沙,白鹭用飞翔的标识
咬住一场江南雨的来龙去脉
当它将脚落在春江上起舞照影时
实际已完成了身体的伸展抒情
而孙氏后裔,在遗传真迹上重塑
后人凭借孙坚父子的挥刀血性
在三国历史隐入密林前
为洋涨沙塑上王洲的金身
在更多的时候
作为后代,我们说出他的盖世
还要带上一种软骨的哀伤
在两者之间,寄居着真实的性情
而无数泡沫在演义中聚会碰杯
洋涨沙收藏了最后一口耿直
当沉潜的泥沙露出金身
寒冬中培植的炊烟与热血已复活
而皇家的延续无需查询
它已裂变出无数乡野的蓓蕾
沃野、野花和乡村被审美观点燃
让子孙寻找蓝天穹顶的故乡系统
让每次亲密拥抱的圆弧线粒体
都无限接近我笔尖美好的触动

场口的春天
东风吐出了花信。油菜花
从东梓关、洋涨沙、青江口
肆意横开
一直把春天逼到了
富春江南岸。蛮不讲理的花香
在场口的田野里
撒野翻滚
如果你不小心,还会在
一个个村庄外撞上桃花
那一片片青春的粉红
正从春风里溢出
却按不住鸟鸣的漾荡
引得桃花一树树欢叫
场口的春天
——多么简约的春天
只是剪了一段春风
就扶起了每一株花草树木
留下吧!匆匆的脚步
看!绽放的田间地头
如潮的花海,在风里使劲点头

作者简介:孙亚军,笔名老树,杭州人,高级教师,有诗发表于微刊与纸刊。
(作者:孙亚军2024-05-10发于现代诗歌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