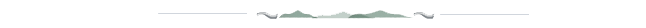昨晚,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自己回到很小的时候,约摸着五六岁,跟另外一个小伙伴倚靠在土砖房的围墙旁边,双手相互捅进袖管里,但是却怎么也想不起小伙伴是谁,小伙伴的脸是什么样子?似梦非梦,但却格外的画面清晰、真实,却也真实的回不去了。因为,真实的拿“栏丫条”的人远去了,不像梦里那么清晰。
大厅的一侧,自行车没有反抗,斜靠在椅子上,只有后轮连着地,前轮被取下来了,龙头无力的歪歪的耷拉着,空空的,显得分外的无助,兀自的斜躺着,二哥在惆怅的看着被自己拆坏的二八大杠,就一直木木的盯着自行车,偶尔退几步,时而往旁边弯下腰,时而侧着身瞄准着什么,眼睛始终都直勾勾的瞅着拆卸下来的“犯罪现场”,眼神里写满了惊恐和疑惑,什么话也不说,连起码的嘟囔都没有,可能是在考虑接下来的逃跑路线(原则上来讲,装不回去难免要被一顿胖揍)
想想,这已经是第四次拆卸物件后,还原不了了,排第一的是二伯几乎天天不离身的收音机。天线可以随意旋转和拉伸的那种,银白色,正面有很多原型小孔,机身旁边有声音的调节按钮和调节接收信号灵敏度的齿轮,底部有个挂扣,拴着一根黑绳,黑绳上有一枚父亲篆刻给他的小印章,用的是7号电池,就在转身去拿茶杯泡茶的空挡,被二哥他们劫持,本想看看神奇的收音机从哪里发出来声音,估摸研究完了给二伯送回来,连说辞都想好了:“看着二伯的收音机很多灰尘,我们给它“收拾收拾””。然而,说辞什么的却没能情景再现,收拾收拾中也就真的被收拾了,连小型的螺丝刀和镊子等作案工具都没有,居然拿着剪刀就开始拧螺丝,握着撬杠就开始拆面板,螺丝自然是滑丝了,面板的扣也不知道在哪,自然也是被翘的面目全非,等缓过神来之后,发现怎么也盖不上去,面板的轴也被弄断了,根本合不上去,收音机里面掉出的各种碎片叫苦不迭,有的零落着散布在周边,有的在各个小伙伴手上,有的被攥在二哥发汗的手心里,一起蹲着的小伙伴们七手八脚的比划着,七嘴八舌的讨论着,眼看装不回去了,脑袋里想起二伯那个凶煞的小眼神,都各自回去了,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像极了回到riben却在远东军事法庭上出现的小鬼子。只有二哥“努力”地断后,努力的化腐朽为神奇,惆怅着思索着突然眼睛一亮,站起身翻箱倒柜去了,回来时多了一卷透明胶,嘴角的上扬好像在诉说透明胶可以拯救这个支离破碎的好奇心,二哥自作聪明的用透明胶给把面板装模做样的连起来,趁着夜色,悄悄的放回了二伯躺椅旁边的小茶几上。
眼神本就迷离的二伯,看到收音机回来了,欣喜之余,内心失而复得的庆幸着,双手捧起收音机,食指熟悉的按下播放键,没有声音,侧着头拿起收音机贴到耳边,还是没有声音,把声音调到最大,小心翼翼的转动天线,咔,天线脱出来了,定神一看,收音机浑身被透明胶带缠绕着,只有按钮和天线被露在外面,瞬间脸胀的通红,口若悬河的骂骂咧咧着,猫着腰,双手捧着收音机朝着三伯家踱去(三伯家的淘小子是出了名的,叫金哥,上天入地的淘,独树一帜的淘,花式的淘,成功案例之一就是二伯告他状,把二伯家的南瓜苗整的那一年没结一个瓜,天天盯着那排南瓜苗,见到开花就给它收拾掉,很久都没被发现,直到后来有人告密,此后一出幺蛾子,他便成为二伯的直接怀疑对象),在银锁(金哥的弟弟)的承认下才知道了真相,二伯又气呼呼地径直往我家奔去。。。。。。
“老七,来,看看你家二娃子干的好事,来你看看,好好看看!这可是好不容易托到人买的收音机!你们这是一天好日子都不让人过啊”,二伯激动着,把收音机径直安放在桌上,一直推到父亲跟前的酒杯旁,撞了一下酒杯,酒杯里的酒沿着推力囫囵晃了几圈,酒杯晃晃悠悠还是站住了,差一点被推翻。二伯还在激动着,手指一直指着收音机,眼睛瞪圆着,义愤填膺的样子着实很可怕;
父亲连忙放下手中的筷子,抬起头,起身,挪到二伯前,笑着搀扶着二伯的手,示意他先坐下,眼里满是陪笑,一副讨好的样子,顺手拿着一只杯子,满上,将酒杯递到二伯面前。而后看了看收音机,双手小心翼翼的扶着收音机打量着,仔细的端详了好一会儿,又瞅了一眼二哥,二哥的筷子搭在嘴角,一手扶着碗,一手扶着筷子,整个人僵坐着,眼神里满是乞讨,乞求二伯不要再骂下去了,眼光呆呆地望着父亲。再看了看喘着粗气的二伯,二伯半推半就的坐着,嘴巴继续喃喃的抱怨着,眼睛直勾勾的怒视着二哥,压抑着愤怒,充满着愤慨。
父亲一边假装看收音机,一边朝大门后面寻去,突然扭头一转,双手换单手,左手拽着收音机,右手习惯性从门后掏出“栏丫条”大踏步走到二哥旁,一“栏丫条”下去,如排山倒海一般,应声打在二哥坐的长凳上,“啪”的一声响彻整个大厅,被打断的小碎条四散而弹,只有回荡的声音仿佛在大声告诉二哥,“快跑”!也在提醒着二伯:“你看,我已经开始替你出气了,而且还这么用力,连我的亲儿子都下得去手”,二哥吓得魂都没了,“哇”的大叫一声,丢下碗筷,自顾自的夺门而出,父亲紧追其后,爷两一个后面追着打着,一个前面跑着哭喊着;二伯也兀自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随后无趣的看着,幸灾乐祸的立在门口。追的人在想,儿啊,你倒是跑快一点,别停下来,要不我们这戏就演不下去了,我不好跟我的哥哥交代啊,时不时传来一声,栏丫条扑地的声音和父亲呵斥二哥的骂声;跑的人在盼着,父亲,别打了,我可是你的儿子啊,怎么这么狠心,我都快跑不动了。
栏丫条不时的呼打在地,毫无思想的“无情的”打在二哥的身后,那距离像是被量好一般,不近不远,不偏不倚地就在身后,旁人乍看,一个拼命在教训自己儿子的真实画面,每一次下手都是那么真实那么重,加上每次呼打在地时发出的声响,二哥都以为自己被打到了,然后哇哇大哭的惨叫声重新呼应了这一系列动作,堪称完美;忽然,二哥计上心头,“跑到二伯家去找二伯母求救”,绕了一大圈后,从二伯家后门跑进了二伯家厨房,正在做饭的二伯母见状,连忙吩咐着二哥去柴房坐着,并拦住了父亲;父亲可算松了一口气,脚步便放慢下来,心里嘀咕:“平时属她最宠这小子,还算你小子机灵,知道求救,不然可不好收这个场”;可父亲嘴巴却没饶二哥,“这个逆子,一天天正事不干尽惹事淘气,一点都不让人消停,把他二伯的收音机弄坏了,还自作聪明用透明胶粘起来,糊弄人,今天我非让他尝尝黄鳝肉的滋味”(“黄鳝肉”是形容小孩被栏丫条打的时候,一扭一扭的像黄鳝扭动的画面,比喻挨揍)并装模做样的朝柴房训斥着,在二伯母的劝解下,装模做样的回家去了,一边走着,一边把栏丫条上细长的枝条卷到一起,仿佛在告诉围观群众,已经教训完了,别看热闹了;
二伯的脸色缓和了许多,少了刚进门时候的面目可憎,多了一点和颜悦色,立在门口,有点不知所措,还有点拘谨,又夹杂一些难为情,小碎步来回在移动着,看到父亲回来了,支支吾吾的,还带着一丝丝笑意:“老七,算了,小孩子淘气,稍微吓吓就行了”。“二哥,这是买收音机的钱和收音机,您拿着,再拖人买一个”。说着话,父亲堆砌了一些笑容,用手臂夹着收音机,把栏丫条靠在门口的墙上,翻出口袋里的各种零钱,朝着二伯道。二伯退了一小步,摆了摆手,假装潇洒的说了一句:一家人,算了吧,以后让二娃子陪我。说完,继续猫着腰,一步一步挪向家门,隐隐约约听到他跑调的哼唱着,应该是收音机里常放的曲目。
望着二伯远去的背影,父亲沉思了片刻,脸露出些许欣慰的模样,拎起栏丫条继续卷着,直到卷完,才舒缓了一口气。走到桌旁慢慢端起酒杯,眯着眼,仰起头一饮而尽,好像把这世上难以下咽的磕磕绊绊,通通都让这玉液洗刷殆尽。收音机庄严的竖着,与之前不同的是,那枚小印章被人取下了。回想起二伯摆手时不自然握拳的手指缝里露出的黑绳,父亲的酒没有再续,默默的把栏丫条倒着放回到门后。
到懂事后才明白,因为顺着放回,拿起的时候不需要蹲下去,倒着放回,蹲下去拿的时候,可以给我们逃跑的机会。
而今天,我和哥哥们却多么希望这不是梦,而是他们都健康都健在,多么希望门后继续放着栏丫条,我们继续偶尔能吃着黄鳝肉,他们能继续他们的昆仲情谊,我们也能延续他们的昆仲情谊。梦醒了,声嘶力竭的枕巾却还没醒,它湿着,从进入这个梦的时候开始,就一直湿着,可能会湿很久很久。
(作者:黎书德2024-08-18发于现代诗歌网)